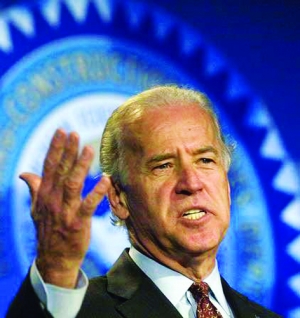为何多数人觉得“被底层”
作者:管健
“向上流动”是蹦一蹦可以摘得到的桃子,而不是翻个筋斗云也够不到的蓬莱仙境的蟠桃
为何底层社会的越轨行为层出不穷
社会心理学家认为,人在欲求不满的情况下会出现被侵犯的感知,而这种被剥夺的感觉会加剧人们的攻击性行为,因而越轨行为来源于其内心的失衡。
社会学家在这一点上又及时补充了社会性原因。美国社会学家默顿认为,每一个社会都给人们规定了从文化上来讲是正确且合法的目标。在理想状态下,社会结构也要为人们实现这些目标提供公平、公正的合法化和制度化的手段。社会的合法目标和制度化手段与人们去实现目标应该是协调统一的,当失调时越轨行为会较多。例如,他分析美国社会为何底层越轨行为层出不穷,是由于大众传播和人们所接受的外在知识从个体小的时候就在传递一种“美国梦”,这种美国梦里有比弗利山庄的洋房别墅和耀眼的劳斯莱斯,但是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达不到梦想的天堂梯。如果人们的梦想越强烈,现实达成可能性越小,那么越轨行为就会越多。
对于中国的底层群体而言,在从平均主义向去平均主义转型的过程中,社会分层的分化与重组,社会财富的流动是必然的。在当今中国,贫富差距的拉大,促使人们内心中显现强烈的不平衡感。底层社会个体的内心中充满了向上流动的渴望,但是社会生活中达成梦想的途径越来越少,或者说存在大量不公平、不合理的现象,这使得底层社会感到迷惘、渺茫,甚至绝望。当社会生活过于强化人们的财富梦想,而相应的社会的合法手段又显现失调,那么底层社会的越轨行为就会增多。
底层人群目前的越轨行为增多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们越来越难于找到向上流动的途径,而且这很可能不是一代的问题,贫困在代际的传递中还会出现世袭的现象。近几年,随着高校收费制度的改革,教育实现向上流动的成本越来越高,贫困家庭中培养的大学生越多其贫困速度可能越快,大量的上学费用需要筹集和借贷,然而毕业后严峻的就业形势使得贫困子女对通过教育而改变命运产生无望的心态。
谁违反了游戏规则
传说在一个偏远的小村落里,村子里长着一棵硕大无比的桃树,村里的居民从古至今都是依靠桃树上结的桃子维持生存。大家每天做的事情就是站在桃树底下蹦起来摘桃子,蹦得高的人可以比较容易摘到桃子,而且又红又大,蹦不高的人只能摘些小的桃子维持生计。但是,大家其乐融融,相对和睦。突然有一天,当人们依旧去桃树下摘桃子,发现村落里一些人违反了古老的游戏规则,很多人踩着梯子去摘桃子,而且这种人越来越多,桃树上的桃子被他们摘得寥寥无几。这种不符合规则的人尽情享受果实,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措施。眼看树上的桃子所剩零星,蹦着摘桃子的人改变了,有些人也去找梯子或者巴结有梯子的人;有些人抱怨,抱怨爬梯子的人不守规矩;还有一些人愤怒,一气之下要掀翻其他人的梯子。
这显然是一个无厘头的小故事,然而它反映的情境和我们却密切相关。在生活中,人们生存的目标就是树上的桃子,每个人都通过个人努力去追求目标。然而,当身边越来越多的人不遵守游戏规则,但是他们却获得了更大、更好、更多的桃子时,其余的人则会感觉被剥夺。风靡一时的电视剧《蜗居》中,姐姐就是一个兢兢业业在树底下蹦着摘桃子的人,妹妹就是那个凭借梯子迅速获得桃子的人。
事实上,从绝对生活条件看,改革开放三十多来,人们的绝对生活有了质的提升。但是人们在生活中,常常结合自己与他人作出的努力,将自己的利益得失和其他人做比较,如果感觉不公平的时候,仍然会出现不公平感,也就是相对剥夺感。默顿曾用“参照群体”的理论来解释相对剥夺感,即关键是人们将哪一个群体视为自己的参照群体、同哪一个群体比较。当今社会,人人觉得自己生活在底层,多数人觉得自己被剥夺,那是因为站在地上蹦着摘桃子的人不满意那些站在梯子上投机取巧、走捷径的人,而站在矮梯子上的人更不会朝地面看,他们眼巴巴地看着那些踩着更高梯子的人在摘取果实。这样,通过社会比较,每个人都存在心理失衡,就都觉得自己是失败者。
从社会层面上来讲,改革本身是社会利益调整的过程,在调整过程中自然会出现利益获得群体和利益受挫群体,全面的利益获得是很难实现的。但是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应该是让每个公民都能看到希望,应该具有满足那些通过合法的努力而获得向上流动的社会结构和社会体系。“向上流动”是蹦一蹦可以摘得到的桃子,而不是翻个筋斗云也够不到的蓬莱仙境的蟠桃。在“蹦”的过程中,游戏规则应尽量公平,所有人都遵守游戏规则,人人心甘情愿的付出努力去获得向上流动,这才是一个公平、公正、合理而开放的现代社会流动机制。(作者为南开大学副教授)
底层抗争的潜在危机
作者:王洪伟
“以身抗争”折射社会制度悲剧
当代中国底层民众的抗争带有鲜明的利益取向,求助于内的“以身抗争”和求助于外的“以法抗争”,一起形成当代中国底层社会抗争的两种最具解释力的社会学逻辑。
一般而言,当社会中的个人遭遇挫折、戕害、磨难的时候,大都寻求两种发泄的途径:如果求解的指向奔向“外在”,而“外在”的制度体系、文化规范又不能有效排解其遭遇的不公、冤屈、灾难,其内在积压的愤懑、不满和怨气难以获得纾解,要么忍气吞声、自我抚慰,要么铤而走险、“以身抗争”,以个人身体血淋淋的毁坏抵制强势的戕害或不公,或者以强势对方甚或“无辜者”的血腥性戕杀或毁灭,引起社会或强势者的重视以求解。
由此可见,“以法抗争”与“以身抗争”是内在关联的,并非前“赴”后“继”的继承关系,即使“以身”抗争的最后一瞬间,抗争者依然抱着“以法”求解的心态和姿态。“以身抗争”行动的曲折只能说是抗争者身处的社会制度悲剧。
抗争行为存在组织化、政治化的潜在危机
笔者在翻阅1990年代以来湖南、江西、广东的“群体性事件”文献资料时发现,即使在1990年代,湖南、江西、广东地区的农民抗争行动由于“在地”民间知识分子的介入,不少抗争行为具有相当的组织化程度,形成以一些具有明确政治信仰的农民精英代表或相关领域的公共知识分子为利益代言人介入其抗争行动。在利益同质性比较高的农民抗税费行动、工人要求涨薪的罢工行动中,组织化的政治性色彩愈加突出。
在当代中国现实中,无论“以法抗争”抑或“以身抗争”,主要起因于基层执政者与“在地”资本强势的结盟;当集体性“以法抗争”止步于纠结深重的地方权贵结盟,追随而进的集体性“以身抗争”就具有更多超越政治性可能,这种集体性的身体恐吓、威胁更有扩张放大和社会号召性效应。如此一来,“以身抗争”的冲动和动力很难在个性化的、功利化的利益诉求层面嘎然而止,个体激愤、苦难和遭遇一旦超越个体的躯壳,融汇到某种“群体精神”之中,以集体抗争平服个体遭际,也就可能在抗争行动性质灌输进某种特殊的可能性;而且,在这个层面上,“以身抗争”较之“以法抗争”带有更大的彻底性、破坏性和颠覆性。
学术界一直以“利益之争”评价当代中国底层民众的抗争诉求,实际上大大淡化了当前中国底层社会的抗争诉求本质。“我不是为了钱,我是为了一种说法!”秋菊打官司打到最后已经不是简单的“赔偿金”问题,而是“那口气”了;一旦“这口气”汇聚成一股或一团气流、声势,进而上升到某种共同意义、普遍信仰,这个社会的正常秩序也就到了危险的边缘,不能不警惕。(作者为河南大学教授)
精英主义束缚底层政治
作者:于建嵘
众多研究者主要还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坚持精英主义的价值观,自上而下地看待底层社会,真正来自底层的眼光微乎其微
长期以来,“底层社会”可以说是被遮蔽及忽视的另一个世界。着眼于底层社会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结构,深入底层人群日常生活的细节和事件,将有助于揭示和再现社会运行的深层动力和被“隐蔽”的社会事实,有助于理解和揭示社会转型背后的另类社会现实,对于丰富社会转型和社会结构以及社会冲突理论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底层政治有自己的“自主性”
一般认为,印度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没有发生激烈的全国性革命,虽然有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但社会底层没有被作为一个阶级整合起来的经历,因此缺乏阶级认同背景下自主的抗争意识。但在印度庶民学派看来,精英主义历史观关于统治与被统治的权力从属关系的分析,忽略了被压迫阶级自身独特的政治。在任何情况下,底层政治的目的、战略和方法与精英主义的都不相同,底层政治有自己的“自主性”。特别是,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帕沙·查特吉教授通过对欧美学术界流行的国家与公民社会理论的系统批判,提出了底层政治研究的核心概念——政治社会。他指出,以欧美历史经验为主所延伸出来的国家与公民社会分析框架并不足以描绘与解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真实状况。
现代国家在治理的过程中,发展出了针对不同“人口”群的治理机制,这个治理机制给弱势人口在实际的社会关系中创造非主流政治提供了民主空间。这些人口不是国家的也不是公民社会的主体,他们的存在甚至被认为非法的,或是要在现代化过程中被清除的,也因此基本上被排除在正轨的政治参与过程之外,最多不过成为社会精英动员的对象,在权力分配完成后,继续被统治。但是,在许多情况下,为了生存他们必须不断地与国家和公民社会周旋。在这个周旋过程中,他们的目的不在于夺取国家机器,也不在于取得公民社会的领导权,从而开启了一个中介于两者之间极为不稳定的暂时空间,称为政治社会。这些来自下层人口的抗争其实是后殖民时期主要的政治活动,只是国家精英不以“政治”来对待他们。实际上,底层民众的斗争影响着社会的发展和民主的进程,是真正意义上的政治。
众所周知,中国在争取民族解放的过程中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先后经历了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其中共产党领导的以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为指导的革命,进行了广泛的社会动员,很多处于社会底层的工人、农民参与其中,形成了具有阶级认同的底层意识。虽然这种维系底层群体身份认同的革命遗产在当前的中国社会仍有很大的影响,但是众多的研究者主要还是站在精英的立场上,坚持精英主义的价值观,自上而下地看待底层社会。真正来自底层的眼光微乎其微,就是那些对边缘弱势群体问题的呼吁,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这样一种危机意识:底层生存状况的恶化会影响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显而易见,在这样一种自上而下的对危险警示的精英思维的反应中,底层是作为治理对象和防范对象而存在的。
底层政治是反应性或应对性的
如果说,精英政治是与国家政权相联系的,并通过有组织力量的国家政治而经常表现为制度或秩序,表现为强制性的手段,以及精英们无论是否掌握了国家权力,都试图塑造自己的合法性并使之意识形态化。那么,底层政治则更多的是底层民众的自发行为,其行为方式则可能是隐性的、自发而零散的。这有如斯科特所说,“它们几乎不需要协调和计划,它们通常表现为一种个体的自助形式,避免直接地、象征性地与官方或精英制定的规范相对抗。”同时,底层政治是反应性的或应对性的,它是对现实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满寻找解释的方式和解决的路径。其中,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利益受到损害。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利益诉求都可以成为底层民众进行抗争的诱因。它需要对自己利益受到侵害有明确的感知。在目前的中国,底层民众进行集体行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以意识形态和其他社群为参照而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以法律规定为依据而产生的利益受损感。前者如工人对企业改制的不满讲的就是“理”,后者如农民因土地被非法征用依据的就是“法”。
要了解底层社会就是要走进他们的生活,从底层群体的处境去理解他们的诉求和行为。也就是说,我们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政治精英活动的层面上,而是需要深入底层社会生活的内在结构中去寻找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这就要求我们的研究必须摆脱精英主义价值观的束缚,树立全新的底层立场。对那些主导社会发展的精英不能简单地停留在道德评价的层面上,而是需要寻找一种制约精英们行动的社会力量。毫无疑问,这种力量首先来自政治背后的社会群体的利益关系,然后才是制度的设定和遵守。在这里,民主政治的主要意义,就是让政治精英和底层民众在内的社会各群体有一个平等的利益表达平台。(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